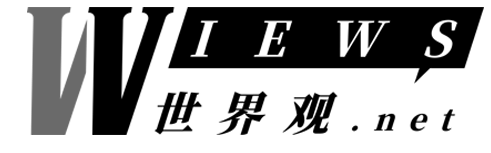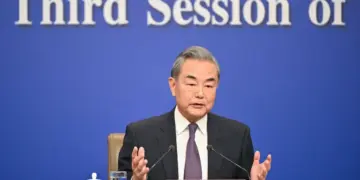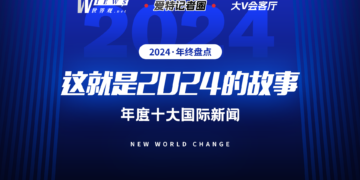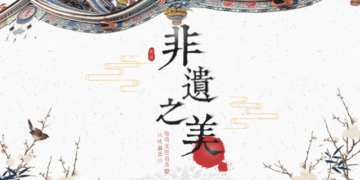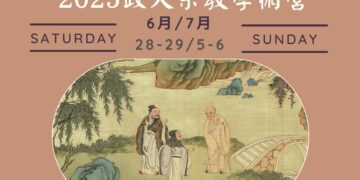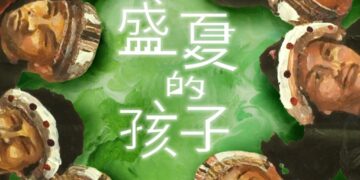三年疫情过后,中国电影在2023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票房成绩单,全年549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已经逼近2018、2019时的高点。而不太为公众所关注的是,2023年的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既有《流浪地球2》这样的大制作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上映,更有《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等影片在海外一些地区打破历史记录的战绩。呈现在海外观众面前的中国电影,不再只有功夫片、古装武侠片,科幻、悬疑、剧情等类型也开始拥有一席之地。
相比国内的电影宣发,一部电影的海外发行其实是一项有着自身商业逻辑的“技术活儿”,中国电影能于2023年在海外发行上取得不俗成果,离不开行业里每一位为之付出努力的从业者。
专注于中国电影国际版权发行的齐放娱乐创始人丁小寅就是其中一位。近日在接受世界观Views专访时,丁小寅对于行业在2023年的际遇颇为感慨,脱口而出了“浴火重生”四个字。
的确,疫情三年里,中国电影相关产业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与打击,海外发行作为电影的下游产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丁小寅表示,从国内来看,疫情三年期间中国电影的产出量大幅减少,海外发行从源头上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国外的市场环境来看,世界各国普遍都经历过影院关闭的时期,即便后来开放了电影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都不愿意去密闭空间观影;作为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大量中国留学生无法去到国外,海外的观众群体也大幅减少。

疫情下影响中国电影市场
内外交困之下,疫情三年期间中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惨不忍睹”,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丁小寅估算那三年的海外票房“能有2019年的20%就不错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电影在2019年的整体繁荣让海外票房冲上了历史高点。
这也让中国电影海外发行在2023年的强势反弹显得殊为不易。对此丁小寅表示,产品质量是销售的基础,2003年至今不超过20年间,中国电影业更新观念,调整思路,推动了电影业向产业化道路上的迈进,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20年做到了好莱坞可能100年才能做到的事”。她认为,国内出产的影片在硬件条件与技术能力上,“包括拍摄的机器、置景、美术、一般特效等全方位的,已经不输好莱坞。”在质量有保证的基础上,海外对于中国电影的观感已经比过去有了“重大提升”。
而如同所有商业领域的通行逻辑一样,工业水平上乘的电影想要在海外卖的好,也需要销售领域的发力,毕竟产品好和卖得好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丁小寅讲述了其中的诸多“门道”:那些在国内高成本、大制作、高票房的“大片”,通常在北美、澳新等华人扎堆的地区也会有不错的票房,但国内票房数字和海外票房、版权销售的数字也常常会有令行业外意想不到的反差,比如以语言为主要笑点的喜剧片在海外就比较难卖;受限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一些在国内讨论度很高的影片可能会让海外某些地区的观众觉得“看不懂”;由于语言、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拉美地区的版权销售情况往往取决于西班牙、法国等地的分销商等等。
在丁小寅看来,做海外发行,需要对经手的每一部片子“用120%的努力”,尽可能做到“私人订制”。她表示,那些“声势浩大的大项目”,当然容易在海外票房出成绩,容易被大家看到,但自己很多时候更在意那些“国内票房1亿以下的‘小项目’”,“以现在的国内电影行业来讲,这种项目连腰部项目都不算,但要给这样的项目在海外发行上找一个合适的定位、合理的打法并不容易。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反正是‘小项目’,就随便做一做,反正国内票房本来就没有那么高,片方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无所谓了,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想。”
在这样的坚持下,丁小寅已经留下了多个以小搏大的案例。“如果非要举个例子,2023年我对《爱很美味》这个项目印象很深。我不能说这是我给自己评价最高的一个项目,但肯定是给我带来‘惊喜值’最高的项目,它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对得起我们自己付出的努力。”
《爱很美味》从同名的电视剧改编而来,由于剧版的海外版权卖给了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丁小寅在操作这个电影项目的时候也首先联系了网飞。“像这种片子的国内票房体量在那儿放着,片方对它的海外销售预期肯定没那么高,但我们可以说是深挖了这个项目的潜力。”
“如果图省事,直接卖给网飞肯定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做法,也能达到一个没有过错甚至还能有点小功劳的结果,但我们在和网飞谈判的时候刻意保留了泰国等一些地区的线下发行权,因为我们凭经验觉得这种‘小妞电影’和泰国流行的女性向青春爱情片很像,当时就说一定要把泰国(的院线发行权)留下。很巧的是,谈完了以后我们又发现影片里一个主要演员是中泰混血,在泰国还有很多粉丝。最后证明,这部片子在泰国院线的上映做的声势非常大,票房大大超出预期,好多那种几百人的大场次都是坐满的。泰国那边的发行商把他们制作的影片周边也送了我们几份,一看就知道做的非常用心。”
这是丁小寅的经验之谈中最重要的一点:任何一个项目,如果没有一开始不嫌麻烦的坚持,就不会有最终圆满的结果。“我们做过的片子,我不仅希望它在北美、澳新卖的好,我希望它在欧洲也能卖的好,在拉美卖的好,在中东卖的好,包括在蒙古都要做专门的上映安排——蒙古全国只有6家电影院,乌兰巴托有4家,其他地方有2家,在咱们国内一个县城都不止6家电影院了,咱们都很难想象。我们希望每一个经手的片子都能走得很远。”
这个话题里正好涉及到电影海外发行的新阵地“流媒体平台”。丁小寅回忆,2019年她将《流浪地球1》卖给网飞(Netflix)的时候,国内对于流媒体平台的认可度还不高,甚至认为在网飞播放并不算是“发行”。但事实上,当时网飞不仅非常用心地给影片做了数十款海报,而且会根据不同用户的观看记录和习惯,会呈现不同主打元素的推荐页面,还为影片制作了27种语言的字幕,可以说有效地让全球很多观众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科幻大片。
到了今天,很多国产电影开始流行将海外版权卖给网飞视为某种“荣誉认证”的时候,最先吃螃蟹的丁小寅反而开始反思:“我会经常想,如果当时《流浪地球1》也是在网飞那里留下(线下)空间,是不是会有更多可能性,因为我们在操作《流浪地球2》的时候发现,由于没有在海外做大规模的院线发行,导致海外市场对‘流浪地球’这个IP的认知度不够高。”她还提到,没有必要将网飞神化,“烂片确实大概率不太会被网飞选择,但也不是网飞上的片子就都有多么好,它有一些艺术水准高的,也有大量的爆米花电影,它的选片基于它的算法,毕竟网飞的基因是互联网公司。”
由于文化上的隔阂,能在海外取得好成绩的中国电影,长期以来都是功夫、仙侠等题材,而在2023年,以《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等悬疑片在全球多个地区票房火爆,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某种新动向。
在丁小寅看来,中国电影在海外的“类型突破”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还是影片质量的提升,“特别是随着2017年左右‘热钱’从电影圈退潮,今天已经不是随便一个什么项目都能得到大笔投资的时候。每年立项的电影有很多,今天能从众多项目中进入国内院线的,绝大多数在工业水准有保证。”
其次,国内已经较为完备的实时票房数据统计系统,让海外的买家们有了最方便也最精准的参考——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目前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的各个国家,别说“灯塔”这样的专业数据平台,就连“猫眼”这样的实时票房数据都没有。能够让全民随手查阅票房数据的,全球只此中国一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沿袭影院向第三方机构上报售票情况的老方法,“是一个特别不透明的系统”,民众要想知道哪部影片受欢迎,只能依靠新闻中对电影院上座率的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感知。
中国国内相对完备的票房统计系统,可以让海外发行商通过历年数据的梳理形成选片依据,更为商业上的及时反应提供了抓手。“《消失的她》上映一天后,数据推算最终的国内票房能达到30亿,海外(发行商们)就‘疯了’,好多人打电话过来问这片子能不能做(发行)。”
第三个原因,丁小寅认为,此前“走出去”的中国电影,大多以贾樟柯、王小帅等注重艺术表达的作品为主,“通常会讲一个只会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虽然内核里的人性等元素是相通的,但毕竟存在观影门槛”;而新一代的中国商业片导演们,已经有能力在各种常见的类型框架下去讲好一个“世界性”的故事。
“像《孤注一掷》,在马来西亚打破了多少年以来成龙电影保持的票房纪录,非常吓人。其实这个故事不光是电信诈骗泛滥的东南亚地区的人感同身受,世界其他地方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消失的她》这个片子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北欧地区上映,我专门问过芬兰当地(发行商),他说不存在我们设想中的‘华人包场’的情况(毕竟距离中国国内上映已经半年了),来电影院看的80%都是芬兰本地人,芬兰网络上还有很多关于影片的讨论。这一方面确实说明中国能拍出‘世界性议题’的电影,另一方面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值了。”
能够被看见、能够被讨论,这本身就关乎“话语权”的体现,学者约瑟夫·奈将其归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在民间的认知中,还是官方的期许中,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往往还被赋予了“内容出海”甚至“文化出海”的意涵。丁小寅表示,自己之所以会选择电影海外发行这个行业,来源于自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求学的经历。
“当时整个专业从硕士班到博士班,就我一个中国留学生,剩下清一色都是美国学生。我印象很深的是研究生二年级,开始做助教了,下面一届总算是又来了两个中国学生,当时欢迎新生的圆桌上,老师问大家暑假都看了什么电影,新来的中国学生说了一部在国内讨论度很高的电影,当时国内给那片子一个‘PPT电影’的外号,但说出来只有我们三个中国人在笑,所有美国同学一脸茫然。我们几个解释了半天,美国同学也还是觉得莫名其妙。”
“那一刻我突然就被触动了。”丁小寅说,“南加大的电影学院是全世界公认最顶级的电影学院之一了,但是这里的学生说起中国电影,还是贾樟柯、王小帅,或者早年的张艺谋、陈凯歌。你问任何一个美国同学,中国电影院现在在放什么?中国本土电影票房冠军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也不关心,而那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了。当然,电影学院的学生,去看那些在戛纳、威尼斯获奖的片子无可厚非,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电影院里现在在放什么好莱坞大片。”
“这种强烈的鸿沟感,让我突然明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了。我不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美国同学说起中国电影,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尽管没有了解过国外的电影学院现下是否有了改观,但丁小寅已经在非主营业务上发现了变化:“前不久有个国外社交媒体上的大V博主联系我们,他是个在网上教外国人说汉语的网红,想要在教学中用这两年的一些中国电影的片段作为教材,告诉他的学生说,现在的中国人对于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时兴的表达,电影肯定是一个最直观、最有时代性的素材,所以问我们关于授权方面的事。他有这个想法也是跟他学汉语的外国人很有这方面的兴趣。”
能在此时此刻与世界范围内的各个人群发生连结,这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或许就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东西”。
当然,再宏大的发愿也需要落实在具体的操作上,在丁小寅看来,海外发行的行业还不算成熟,自己所有的努力仍是为后来人“打基础”的阶段。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行业能够更加规范:“我要求自己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扎扎实实的,更要求自己不可以在放映银幕数、观影人次、线上播放量等数据上作假。正因为还处于蓝海,行业更需要统一的标准与规则出台,让大家多做对中国电影有益的事,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去做有害的内卷。”
记者:李翔
责编:杨语涛